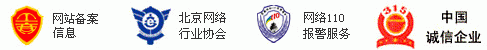2020年世界貿易組織全球機床行業數據出爐,中國機床產值和消費額分別為169.5億歐元與186.1億歐元,均為世界第一。這是中國機床產業自2009年首次成為世界產值第一之后,再一次向世界證明,我們是一個機床大國。
然而,人們不禁疑問,從2009年到2020年,中國是否已經從機床大國,變為機床強國?
2008年,世界機床產值排名前十分別為:德國通快、日本山崎馬扎克、德國吉德曼、日本大隈、日本天田(AMADA)、美國MAG、日本森精機、中國沈陽機床、日本捷太格特(Jtekt)、中國大連機床。前10當中,德國2家,日本5家,美國1家,中國有2家。
13年之后,世界前10大連機床床企業中,德日依舊霸榜,兩家中國大陸的機床企業卻被臺灣企業所取代。更令人唏噓的是,中國機床行業的四大支柱企業——沈陽機床、大連機床紛紛并入通用技術集團,昆明機床也已退市,只余秦川苦苦支撐,離世界前10的距離越來越遠……為什么在產值、消費額均為世界第一的今天,我國機床依然“大而不強”?
機床行業的意義重大。對于高科技行業而言,機床是現代工藝技術的集大成者,沒有先進的加工技術,就沒有現代制造的核心競爭力;對于國家而言,機床行業是國之重器,屬于立國之本,沒有自主創新的高端機床就沒有做世界一流強國的資格。
短暫的輝煌
我國機床行業起步并不晚。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蘇聯專家建議下,“一五”時期,國家對部分機修廠進行改造并新建了一些企業,其中有18家企業被確定為機床生產的重點骨干企業,被業內稱為“十八羅漢”。
它們代表了當時我國裝備制造業乃至整個工業發展“母機”最高水平,也曾創造出了無數個機床行業的第一:新中國第一臺車床(沈一機)、第一臺臥式銑鏜床(沈二機)、第一臺數控龍門銑(齊二機)、第一臺三座標數控龍門移動式銑床(北一機)……
“十八羅漢”及其專業分工
1958年的秋天,當朝鮮勞動黨主席金日成在周總理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地來到清華大學的車間參觀時,等候多時的師生們熱烈歡迎了這位異國客人:沒有用鮮花,沒有用掌聲,而是聚精會神的操作著一臺結構復雜的機床,加工著什么。
不一會兒,一塊刻有“金日成萬歲”五個字的鋼板被遞到了金日成的手里,他立刻饒有興致地接過來,撫摸著,詢問著。隨后,又一塊寫著“毛主席萬歲”的鋼板被遞到了周總理的手中。金日成主席對這一先進的技術贊不絕口,立刻題詞留念。這臺完成了刻字的設備就是我國第一臺由清華大學和北京第一機床廠聯合研制的數控機床:X53K1。
1958年我國第一臺數控機床X53K1
彼時,掌握“數控”這種尖端技術的工業發達國家對中國采取絕對封鎖的政策,在沒有樣機和可供參考的技術資料的前提下,平均年齡只有24歲的科研人員,包括教授、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學生等,只憑著一頁“僅供參考”的資料卡和一張示意圖,僅僅用了9個月的時間便攻下了一道又一道的難關,研制成功了數控系統,由它來控制機床的工作臺和橫向滑鞍以及立銑頭進給運動,實現了三坐標聯動。
設計出我國第一臺數控機床的團隊成員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要知道,研制成功數控機床,美國用了4年,英國用了兩年半,而日本當時尚且沒有完全掌握技術,還在摸索中。
可以說,當時,我國與工業發達國家在機床領域的差距僅在五年左右。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機床行業與發達國家差距被逐步拉大。
蘇聯解體的30年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告解體,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徹底從世界舞臺中消失,全球軍工市場出現了失衡,間接導致世界機床行業發生變革。
為什么?機床是制造業的基礎,制造業是軍事工業的基石。軍工市場需求的突變,導致無人采購高端機床生產軍工用品。1994年,德國最大的三家機床廠德克爾、馬豪和吉特邁紛紛出現虧損和倒閉的情況。為了挽救危機,吉特邁整合德克爾和馬豪兩家公司,合并組建了德馬吉機床集團。三大廠商的“捆綁”帶來了技術優勢和規模優勢,在市場化的推動下,德馬吉不僅很快將技術轉化為新的生產力,迅速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
在西方工業力量重構之時,遠在東亞的中國剛剛結束了計劃經濟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強調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形式,調整國家與企業之間的生產管理權限與利益分配關系,在企業內部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
到1990年前,我國機床行業共有8個綜合性研究院所、37個專業研究所與企業設計部門,已經形成了機床工具行業科研開發體系。在國有企業改革的浪潮下,建國初成立的十八家國有機床骨干企業不是改革轉制,就是破產重組,“七院一所”也轉型為企業,各謀生路。原有的機床科研開發體系被打碎。
為了推動市場化發展,1998年,擁有4600多人,管理900多家企業的機械工業部也被撤銷。
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為了生產更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中國一些企業不惜高價大量引進日、德、美等國的數控技術,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濟一機床與日本山崎馬扎克率先合作,開創了機床業國際合作的先河。之后,沈二機與德國沙爾曼、齊一機與德國瓦德里希·濟根等紛紛合作……學習國外先進技術,讓“十八羅漢”一度功力暴漲。
這種引進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些企業獲得了技術,但原有的機床體系受到了沖擊,自主創新能力的進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大跨步前行的同時,也給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打來了隱憂。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制造業井噴,機床需求暴漲。作為中國機床業“領頭羊”的沈陽機床趕上前所未有的好時代,一路高歌猛進:2004年吞并云機、昆機,壟斷車床、鏜銑床市場;2005年,再并購德國希斯,力圖掌握數控機床高端技術。
2008年,沈陽機床、大連機床在世界機床企業產值排名TOP10中,分別位列第8、第10。濟二機床成了“世界三大數控沖壓裝備制造商”之一,讓中國大型汽車沖壓產線,闖入了美國福特、日產北美、法國標致雪鐵龍的制造車間。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的全球機床排行榜上,沈陽機床已以180億元的銷售額,問鼎世界第一。
“雖然從表面上看,2001年之后我國機床業迎來‘黃金十年’,行業總產值暴漲10倍,但是大多數企業片面追求數量和規模,把技術研究放在了第二位,而且原來的學徒制沒有了,工人都是合同工,過度追求經濟效益,工匠精神也都丟失了。更可惜的是,原來完整的工業研究體系因為改制土崩瓦解,只剩航空航天和軍工的研發體系較為完整。導致我國機床與國外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原來可能差5年,現在要差15年。”瑞士托納斯機床大中華區總經理單錫林先生說。
但當中國市場告別井噴式增長,重新回到增量有限且全球企業激烈競爭的常態,中國機床業的各種短板再度暴露無遺。曾經快速發展的幾家領軍企業,轉眼成為衰落最快的反面典型,并在最近兩年集體進入“告別演出”時代。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規模以上機床企業15.1%虧損;2020年上半年,這個數字進一步擴大到24.1%。中國機床業曾經的“四大天王”,老大(沈陽機床)、老二(大連機床)破產重整,老三(秦川機床)也陷入嚴重虧損。
此外,從整個行業來看,中國高檔數控機床的國產化率不到10%,90%以上靠進口,我國機床在高端領域被國外企業全面壓制。五軸及以上加工中心自給率不到10%,其中龍門式加工中心及立式加工中心等的自給率甚至不到1%,材料、刀具、冷卻液等絕大部分依賴進口。
眾手扼喉
中國機床行業出現這樣的結果,有以下幾點原因。
1)核心技術缺失
1996年,沈陽機床耗資上億元,引入美國橋堡的數控技術,但外方只發來一個源代碼數據包,卻不告知核心技術原理及使用原理;2005年,沈陽機床買下德國希斯,以為技術到手。沒想到,德國法律規定,“本土知識不得外移”,五軸以上機床技術更對中國禁運。2007年,沈陽機床打算用6000萬歐元,買下一套數控系統源代碼,但專家一論證,解讀要5年,產業化再5年,技術都過時了。
其實,出于政治和科技安全考慮,德國聯邦經濟和出口管制局一直對機床出口有著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嚴格限制出口機床的精度;另一方面,對出口機床用途加以嚴格限制,高精度機床不向我國軍工企業、教育機構和機床廠出售。
日本通商產業省(MITI)也有類似政策,并且日本企業也有相應的保護措施。
2)外國企業打壓
凡是中國不能自主制造的,國外品牌便高價出售或禁售;凡是中國實現自主突破的,國外企業立刻低價傾銷,讓中國企業巨額的研發費用打水漂。于是,中國企業陷入“高端畏難,中端乏力,低端仿制”的尷尬境地。
在高端領域,我國機床企業對于一些高端行業的需求,連碰都不敢碰。比如在近年的主機廠招投標過程中,有大量的生產綱領及CPK、CMK(CPK,CMK,這些指標主要考量的是對生產設備能夠滿足要求及穩定性的能力評價)等條件嚴格的驗收指標,導致大陸廠商知難而退,參與產線機床競標的企業幾乎全部為德國、日本或瑞士企業,偶爾可以見到中國臺灣和韓國企業,但極少有中國大陸企業參與競標。
在中端領域,日本機床以其可靠耐用的性能以及較便宜的價格牢牢占據了我國的中端市場。以臥式加工中心為例,日本森精機、山崎馬扎克、日本大隈等企業占據了我國超過80%的市場。在吉利、長城等國產汽車品牌的產線中,十余年前便已是德國、日本機床的天下。
在低端領域,一邊是大量中小民營機床企業,聚集在山東滕州(中國中小機床之都)、浙江玉環(中國經濟型數控車床之都)等地,陷入低端混戰。另一邊是,企圖打破國外壟斷的大型企業,他們在投入巨資研發成功后,產生不了利潤,陷入“越創新、越破產”的困局。
3)違背產業規律
機床行業是高技術門檻、高專業分工而且需要長期積累的典型。德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學徒制、雙元制等教育體系為制造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質量“新鮮血液”,同時企業嚴謹務實,追求在“窄領域”做強。在這一基礎上,德國誕生了1300余家單項冠軍企業,為德國高端機床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豐沃土壤”。
日本企業更加崇尚代際傳承、技術傳承,不做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追求精益求精。在這一文化的主導下,日本現有長壽企業數量高達3900家。其中,大量著名機床企業的壽命已超百年,綿延幾代人,歷久不衰,比如山崎馬扎克(成立于1919年)、發那科(成立于1956年)、森精機(成立于1951年)等。
而中國的機床企業,但凡有了一定的成績,就會走上“貪大求快”的道路,沈陽機床、大連機床都是因此走入“萬劫不復”的艱難處境。比如,沈陽機床曾砸出10多億打造出世界上第一款智能化、互聯化數控系統——i5,并在i5推出后推出i5數控機床。時任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甚至提出要把i5鍛造成機床業的“蘋果”,顛覆機床業商業模式的宏圖,但最終卻被證明是步子邁太大:到2016年年初,i5已獲得10000臺超級訂單,但當年沈陽機床卻巨虧14億元。
導致巨虧的原因集中于兩點:一方面,為了快速占領市場,沈陽機床定下以租代售的策略,結果導致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沈陽機床還長期短債長投搞研發與擴張。僅2017年,沈陽機床實施了92.51億債轉股,依然難解現金流枯竭和債務暴雷。
4)工業基礎薄弱
我國工業基礎不牢、“養分”貧瘠,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我國缺失了完整的機床產業研發體系,嚴重制約了我國機床行業的發展。在上游設計、制造端,我國在材料、零部件以及經驗等方面基礎薄弱,難以支撐我國高端機床領域實現全面自主;在下游應用端,離開了進口原料,高端機床在我國如同“廢銅爛鐵”一樣無用武之地。
僅以材料為例,我國基礎材料均質性、切削性能等指標較國外有較大差距,不僅高端刀具依賴進口,大量下游應用端的高端材料也嚴重依賴進口。北京某廠曾斥巨資購買瑞士機床,但使用國產料進行驗收測試時(棒料,公差h7級),經過三個月嘗試,無論如何無法通過測試。與廠家接洽后,廠家用瑞士材料進行加工測試,一切正常。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我國機床行業被歐美日等國迅速甩開,趕超乏力。
拆解“著力點”
目前,發達國家在機床行業全面領先,而我們在許多基礎共性領域仍然出現明顯短板。根據我國機床工具協會數據,從技術上看,我國與國外機床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加工精度;可靠性;機床內部的電、氣、控制系統等裝置;加工速度;外形;智能化。
1)加工精度
機床是一個復雜的機電信息系統,在加工過程中會受到靜力學、動力學、振動以及熱的影響。僅以內部熱影響為例,它包括電機轉動切割磁感線生熱、絲杠導軌運動摩擦生熱、切削過程生熱等數十甚至數百項影響因素,而產生的熱量又會造成零件的受熱變形,造成刀具及材料性能的變化,最終疊加體現在加工誤差上。
歐洲在這方面已經能夠建立起對應的物理模型,能夠通過高精度仿真的方式,模擬分析加工誤差來源,并加以補償,提高加工精度,但目前我國企業甚至對電機轉動切割磁感線生熱這一熱源項尚無有效研究。
2)可靠性
德馬吉森精機(DMG MORI)的返修率有著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數年前,德馬吉森精機公司允許的年返修率已低至1.8次/(千臺*年),這一數據低于我國目前返修率至少一個數量級。
3)電、氣、控制系統
有效、完備的控制系統是機床實現高加工精度和智能化的前提,而完善、合理的傳感器系統則是控制系統的核心硬件基礎。
德瑞日美等國機床企業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Know-How,了解所需傳感器的數量、種類、精度、安裝位置等相關信息,以德馬吉森精機目前市場上的五軸削銑加工中心DMC 80 FD duo BLOCK為例,一臺機床在關鍵部位配備了包括溫度、力、振動、潤滑液流量、冷卻液溫度等在內的超過60個傳感器。通過傳感器,所需的機床及加工信息可以被精準實施的收集,通過適當的控制方法,及時完成在線的修正補償。
4)加工速度
我國機床加工速度慢可以部分歸因于我國的機床設計能力的不足。目前,我國存在大量中小型工廠,其中使用的設備仍為沈陽機床廠的CA6150等簡單機床設備,在一些著名的單項冠軍上榜企業中,車間中大量使用的也是較為落后的90年代的數控機床,生產效率低下。有消息透露,2019年中國臺灣地區的機床企業已全部淘汰手動機床的生產,而沈陽機床1/3的生產線仍然在生產售價僅5萬元的手動機床,沒有全面數控化,導致沒有精力攻關前沿技術,逐漸被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機床企業趕超。
相比之下,歐洲的機床廠商則能夠針對應用場景對機床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和改進。以瑞士著名機床托納斯(Tonors)為例,該廠開發了大量針對細長棒料和針對鐘表中高精度小尺寸零件的加工中心。該公司用于生產汽車發動機噴油嘴的機床,可以完成自動上下料,加工一個噴油嘴只需幾秒鐘,可實現每年數百萬零件的加工量,在保證高精度的同時確保生產效率。
5)外形
過去機床設計都是方方正正的,三十多年前,汽車也是那樣的風格。但是以德馬吉森精機為代表的機床制造商,在2000年開始請意大利法拉利汽車的設計師來設計機器的外形,突出流線型,考慮人機工程學的應用,不再“傻大黑粗”,不再方方正正,雖然也是啟用黑色和深灰色,但是一改過去不是白就是綠以及橙色等顏色,給人一種高檔藝術品的感覺,使操作人員心理穩定,靜下來,不再感覺是在做工業加工。這些年,我國國產機床雖然外形也在改進,在顏色設計上進步很多,但流線型設計還沒做到。
6)智能化
我國機床行業部分從業者對機床智能化的認識仍較淺,某位機床行業的資深專家曾在接受訪談時公開表示,自家機床的智能化就體現在通過手機可以控制機床的運轉。這種將智能簡單等同于“遙控”的思想是不足以指導我國在機床智能化領域完成突破,實現機床“自學習、自適應、自診斷”甚至是“自決策”的。
目前,歐洲的機床企業在智能化的路上已經領先我們許多,以德馬吉森精機的Celos為例,目前這款機器已經能夠大幅優化人機交互,將機床功能組塊化,開發成類似App的功能,用戶可以在面板上更加簡便快捷的進行加工編程操作。此外,Celos已實現加工過程的高精度仿真,加工中心在接收到加工指令程序段后,可首先將加工過程通過建模仿真的方式直接可視化呈現給操作者。
機床智能化的另外一些工作,則需要在完善的傳感器系統的基礎上,疊加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方法實現加工過程、參數、路徑、速度曲線的自動優化,對可能產生的沖突做出提前預警,對內外部干擾因素做出修正補償,保證精度等功能。但不論是大數據還是現階段在機床領域應用的人工智能,都要以大量的經驗數據為基礎。以刀具的智能優化為例,我們可以通過傳感器對其扭矩加以實時監測,并通過扭矩監控破損,如果刀具損壞,切削阻力和扭矩會迅速增大。但是,如果想再進一步對刀具壽命進行預測及磨損進行提前預警的話,則需要大量刀具磨損前的扭矩曲線作為經驗基礎,這項研究在歐洲開展已久,成果顯著。
出 路
機床行業在歐洲受到的重視程度遠超我國,至少體現在高層重視度、行業重視度和社會重視度三個層級。
高層的重視除了體現在常規的科研院所資助、企業研發贊助外,德國總理或總統幾乎每屆都會親臨在德國漢諾威舉辦的歐洲機床博覽會(EMO)。
行業層面,僅以歐洲機床博覽會的規模和專業性為例,在德國漢諾威展覽中心舉辦的歐洲機床博覽會擁有27個場館,占用49.6萬平米室內場館面積,是中國國際機床展覽會(CIMT)的近四倍。同時,高達數十歐元的門票價格也限定了專業人士的范疇,提高了展會參觀人員的范疇。并且每年提出相應的主題,點明了機床行業的發展重點。
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漢諾威工業展
社會教育層面,德國有著完備健全的多級教育體制,學徒制、雙元制、應用科技大學,為工業領域各崗位提供了人才保障,工廠職工有著豐厚的薪酬待遇(2020年德國機械本科畢業生薪資甚至高于IT、經濟和金融),從業者、學生、家長、親朋均對工人及工程師有著高度認同感。
但是,國外機床產業健康發展的共性特征都是成熟的市場化環境。從產業生態角度看,德國國內擁有大量的汽車工業,因為汽車生產需要可以規模化生產的機床,因此,德國很多機床廠便主攻更適合大批量生產的產品,而瑞士則以鐘表和精密制造業聞名于世,因此瑞士的機床廠以生產高精度機床為主。相比之下,我國國有機床企業的企業家大都是行政指派,企業發展往往以完成政治任務為導向。
“中國國內的機床市場,是奧運會賽場,本質上是劇烈的全球化競爭,我們要想走出國門,首先要實現在國內市場的領先。”單錫林給出了“三化一創新”的建議。
1)市場化。我們要大力培養企業家,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企業要首先成為經濟人,鉆研前沿技術,專注于解決“卡脖子”的事情,一切以經濟效益為中心。只有做到產品質量好,給用戶解決實際問題,企業才有利潤。同時也要穩住員工隊伍,這樣才能有傳承。
2)國際化。我們要從全球挑選最一流的運動員組成足球隊,這樣才能做一流的事情。國際化的企業需要國際化的人才,我們除了要從法國、德國、日本引進大量的人才以外,還要去研究德國市場、日本市場、越南市場都需要什么,要思考你在國外市場銷售產品是否也能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務,與外國企業同臺競爭是否有信心?
3)法制化。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識方面,我們差得太多,要按照市場規律和國家通行的準則去行事。我們要重視知識產權,重視公平競爭。
4)只有依靠差異化和創新才能贏得市場。未來機床行業有兩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以智能化生產為目標”和“提高單機標準”為目標。“以智能化生產為目標”即機床將具備通訊功能,實現機床與機床,機床與其它生產設備以及機床與管理中心的實時互聯互通。“提高單機標準”的核心是“更高,更快,更強”。機床的發展始終緊緊圍繞著精度、速度和性能三個核心指標的提升展開,最終達到能夠滿足新材料、新工業的加工需求,實現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增材制造、單機功能的復合化、專用化都是未來的創新著力點。
想象空間
科德數控成功登陸科創板,打開中國高端數控機床自主創新的一扇大門
南京寧慶機床,搭載前沿“數字孿生”技術的橫梁移動式五軸聯動龍門機床
總而言之,本土機床企業要緊盯國際一流企業,將國際一流人才為我所用,專業的事讓專業的人來干,無論國企、民企還是外企都要遵循市場規律。